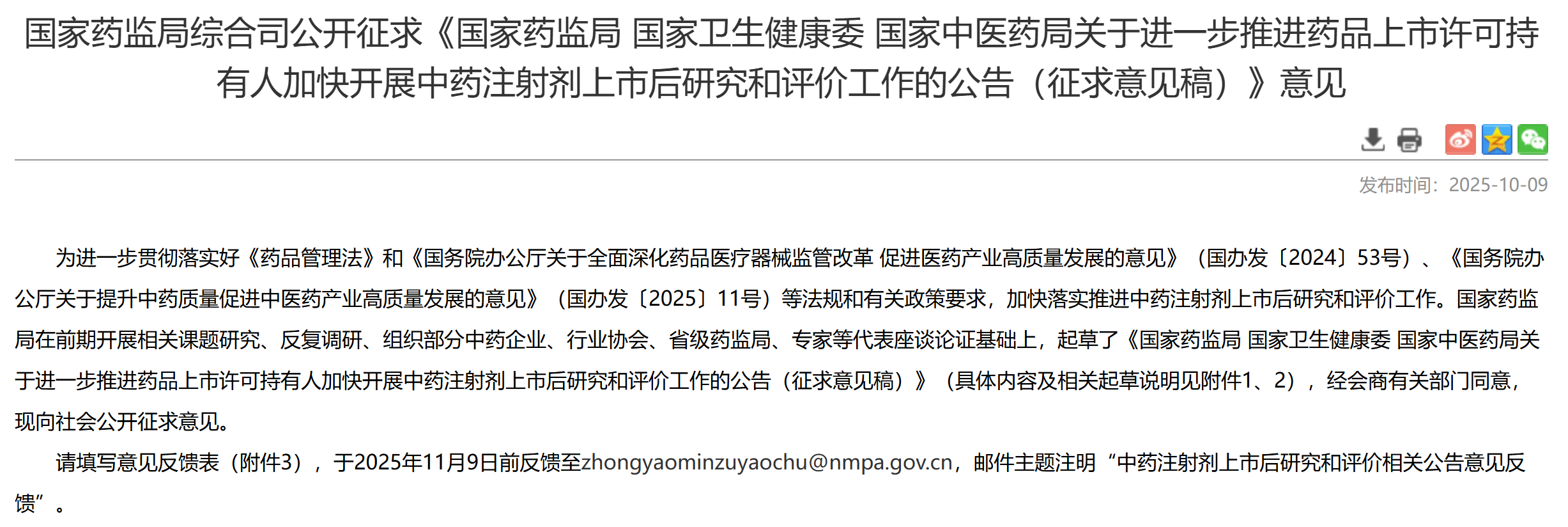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,音乐意识到其演变并非自然有机,不像商业报告中的图表那样逐步递增,反而更像喜马拉雅山——一排若隐若现的巅峰,圈起山间肥沃的平原。这些巅峰是伟大作曲家,这类物种也起源于此。
“伟大作曲家”理论源于托马斯·卡莱尔的想法,他认为世界历史“归根结底是伟人的历史”。穆罕默德、莎士比亚、卢梭和拿破仑是卡莱尔心目中改变世界的人物,而19世纪70年代的音乐家们则意识到,没有威尔第,意大利歌剧将微不足道;没有瓦格纳,德语歌剧也将不复存在。伟大作曲家们撕裂并重绘了音乐世界的版图,就像《纽伦堡的名歌手》所证明的那样。
过去,海顿向巴赫致敬,莫扎特称海顿为“我们所有人的父亲”,贝多芬向亨德尔脱帽,肖邦则将全功归于舒曼,都有各自的鸣谢对象。如今,音乐家们习惯于展望下一位重要的影响者。
在浪漫主义晚期有颇多此类竞争者,从柴可夫斯基到马勒。现代主义则分裂为德彪西-西贝柳斯游轮航线和勋伯格探险之旅。“伟大作曲家”这个理念曾经一度引发过活跃的争论,直到唱片公司抓住时机引领潮流,将所有曾创作过六部或更多交响曲的人打包成“伟大作曲家”合集上架,与从歌德到格雷厄姆·格林等“伟大作家”作品合集摆在一起。文化在走向多元之前,就是那个样子。
然后它就分崩离析。1971年斯特拉文斯基去世,标志着最后的伟大作曲家离世。从此没有可以在饭局上提起的在世作曲家了,大概除了肖斯塔科维奇。肖斯塔科维奇在四年后去世。书架上在那一年之后空空如也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没有哪位交响乐或歌剧作曲家能引起公众的些微关注。英国最杰出的音响大师哈里森·伯特维斯尔(Harrison Birtwistle,1934-2022)逝世,也没能登上BBC新闻头条。伟大作曲家理论堕入了无底深渊,被女权主义者提炼式解读为对死白男的邪教崇拜。
就其他方面而言,这也令人不安。在一个日益专制的时代,我们对新领导人会心存疑虑,而当后人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,他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,寻找那些按照未来标准可能称得上“伟大”二字的21世纪作曲家。
如果你礼貌地向我咨询,我可以提名一两位。你会在爱沙尼亚的某片森林深处发现阿尔沃·帕特(Arvo Pärt),他上个月已经九十岁了,但影响力更胜往昔。苏联时期的帕特曾是一位愤怒的无调性主义者,后来回归饱含沉思的极简主义,以纯粹的精神性嘲讽政权的无神论,并以从容的自然主义回应美国极简主义者史蒂夫·莱奇和菲利普·格拉斯刺耳的重重重复,使后者显得无比都市化,充满焦虑。

作曲家阿尔沃·帕特,摄于2015年4月。视觉中国 图
帕特的《兄弟》和《第三交响曲》这样的作品,初听时便感觉如此永恒,其艺术持久性毋庸置疑。帕特与其作品的存续时间已经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和布列兹主义,也经受住了批判教条和流行变迁的考验。在音乐会上我会一直听到像是帕特的半成品那样的新作。Radiohead与其他摇滚明星都称他为灵感来源。他直面并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,没有丝毫的自我吹捧。阿尔沃·帕特是一位足以跨越时代的音乐家。
另一位沉睡的巨人需要我进行一番自我纠错。在千禧年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嘲讽约翰·威廉斯是“贼鹊大师”,毫无原创性。我当时听的是某部《哈利·波特》电影配乐,从中能够听到马勒、普罗科菲耶夫、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和拉威尔,并进一步借鉴了德彪西(“夜行巷”)、斯美塔那(“科林”)和霍尔斯特(“桃金娘·沃伦”)的主题动机。我当时的分析基于事实,我仍然坚守我的每字每句;但我也忽略了被掩盖的真相:约翰·威廉斯尽管有小偷小摸倾向,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而原创的声音。

2016年4月5日,美国作曲家约翰·威廉斯在好莱坞环球影城的“哈利·波特的魔法世界”开幕式上。视觉中国 图
蒂姆·格里文曾为这位好莱坞顶级作曲家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,指挥家伦纳德·斯拉特金用食指点了点这本书三分之一的地方,表示贝多芬曾用四个音符创作了他的《第五交响曲》的标志性主题。而约翰·威廉斯在《大白鲨》中,却只用了两个音符。他大声宣示:“两个音,你就知道那是什么!单凭这就能让他立于传奇而不败。”
这部五十年前的鲨鱼电影开启了威廉斯与斯皮尔伯格的合作,这段紧密关系堪比莫扎特与达·彭特的默契共生。威廉斯当时年届四十,比斯皮尔伯格大十五岁,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匠人,总有一部戏在手,从未赋闲,直到一场可怕的悲剧中断了他的创作。他的毕生挚爱、充满活力的演员妻子芭芭拉(Barbara Ruick)在拍摄罗伯特·奥特曼(Robert Altman)的一部电影时因脑动脉瘤去世,威廉斯需要抚养三个十几岁的孩子,变得孤僻,几乎不与人交流。
斯皮尔伯格把他介绍给了乔治·卢卡斯,他为之创作了《星球大战》的配乐。他与斯皮尔伯格此后在外太空重聚,合作了《第三类接触》。他的多才多艺令人叹为观止。在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中,并非犹太人的威廉斯使小提琴奏出了意第绪语的哀鸣。他坦言,他的第一个奥斯卡奖源于为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重新配乐。
在一次颁奖典礼中,安德烈·普列文在他耳边催促他离开比弗利山庄,去为管弦乐团创作点严肃玩意。威廉斯迅速回敬了一份勋伯格也会认可的十二音作品。他写过一部半路迷失方向的交响曲,还为各种乐器写过协奏曲,这些作品都获得了票房好评。如今,93岁的约翰·威廉斯可以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,就像古斯塔夫·马勒那样。
他的配乐中没有小品。只要那些电影还在上映,它们的配乐就是永垂不朽的艺术品。无论如何,约翰·威廉斯都是一位伟大作曲家。或许他还能复兴此类物种,并重振人们对管弦乐的信心。